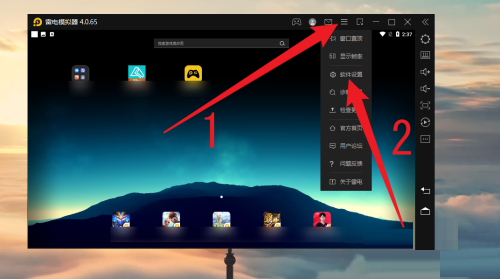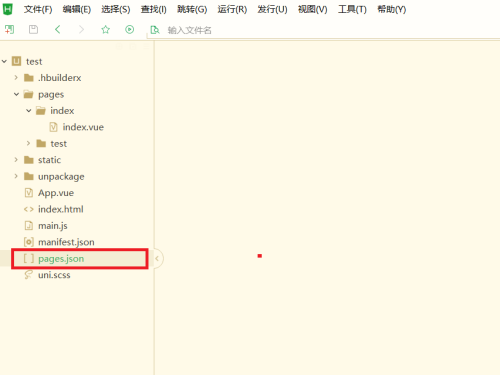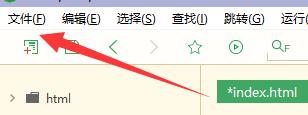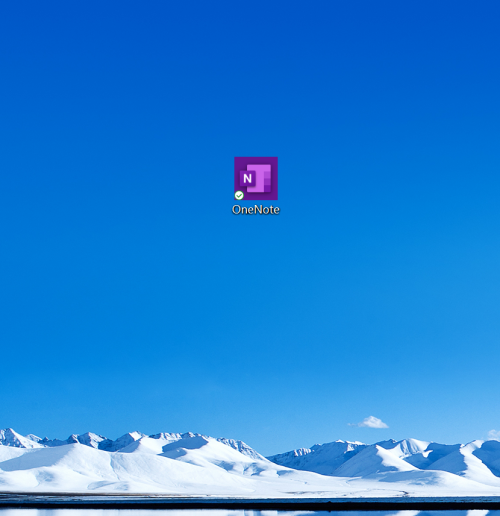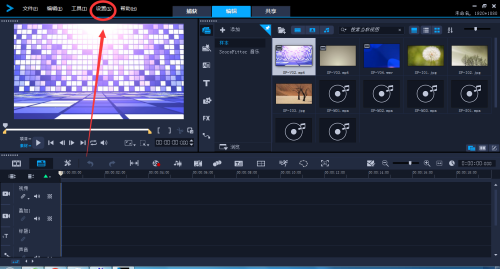只有不到半数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前景感到乐观。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ature Portfolio(ID:nature-portfolio),作者:Asher Mullard,原文标题:《你的工资在国际上什么水平?|〈自然〉薪资和工作满意度调查》,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德国莱比锡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做了一年访问科学家后,Jucelaine Haas在上个月回到了巴西的巴拉那联邦理工大学,Haas说,这份终身教职为她提供了一些保障,但几乎没有晋升的机会。“我是一名大学教授,这听起来是个体面的职称。”
Haas感叹,巴西缺乏资源和机会,难以提供她在竞聘别国教职时所需的竞争力。她说:“你看我的简历,没有太多亮眼的经历,但我已尽力呈现所有。”
插图:Antonio Rodríguez
像Haas这样对前景感到悲观的并不少见。在《自然》2021年薪资和工作满意度调查(见文末注释)中,受资金普遍短缺、就业竞争激烈以及全球大流行病破坏之际的悲观情绪影响,仅有不到半数的受访者对自身前景感到乐观。相比之下,2018年调查时这一比例接近60%。
这项自选调查收到了来自全球研究界的3200余份答复。其中,略多于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居住在北美,25%在欧洲,14%在英国,10%在亚洲。从学科领域来看,有近五分之二的受访者从事于生物医学和临床科学领域,占比最高。近三分之二在学术界工作,15%在产业界,9%在政府机构,5%在非营利组织。
同时,受访者横跨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包括教授和讲师(32%)、博士后(22%)和研究员(19%),近80%的受访者拥有博士学位。此外,女性和男性研究人员的答复人数大致相等,但性别一项并非为二元分类,有2%的研究人员选择非二元性别或不作答。
研究人员对工作前景的乐观情绪似乎正在下降。2018年有59%的研究人员对自身的职业前景持积极态度,今年这一数字已降至47%。此次调查有恰好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职业前景比他们的前辈更糟糕,这个数字倒是与2018年基本持平。
对于Haas来说,留在巴西的缺点之一在于,那里的学者通常不得不承担除研究和教学之外的其他许多职责。例如,她一度得去评估提出自身经济困难的学生的申请。除了本职工作职责,她还要审查财务文件并对学生进行访谈,以确保他们所说财务状况属实。“我不明白这与我的研究有什么关系”,她说。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助理Andie Hall则是对长期职业前景感到不确定。她在同一家机构服务已达17年之久,这一时长已足够她独辟蹊径,为新采集的苔藓动物和200年历史的草蛉标本测序。“我的工作与博物馆里的其他人截然不同”,她说。“我既是技术员又是研究员。这很有趣,但也具有挑战性。”
如果想继续追求上进,她很清楚自己的选项将因为没有硕士学位而寥寥无几。“我经常看到一些招聘启事甚至培训课程,我知道我可以胜任,但他们要博士学位”,她说。“如果你是一名在工作台上解决问题的技术人员,我认为一个博士学位不一定比经验更重要。”
对结果的深入分析表明,职业乐观情绪的分布并不平均。登记为男性的研究人员(49%)比女性(45%)更易对自己的工作前景持积极态度。在受访者最多的10个国家中,巴西的悲观情绪尤其普遍,只有33%的受访者仍感到积极乐观。澳大利亚(37%)和西班牙(38%)的人们感受略好一点。中国(50%)、美国(52%)和印度(57%)的乐观情绪相对常见。
澳大利亚的一位生物医学博士后分享了她的想法:“作为一名拥有超过15年经验的科学家,我对学术已经幻灭了。我的很多朋友都退出了学术圈,我也快放弃了。这不是因为我们匮乏技能或对研究的热情,而是因为必须不断争取才能留在圈中(并以我的心理健康为代价)。”
科学家所在行业也很大程度影响了他们对未来的看法。产业界的受访者(64%)比学术界的(42%)更可能有积极感受。一位来自美国的项目经理写道:“我现在一直给仍在学术界的朋友传播福音,鼓励他们走出来加入生物技术或任何其他专业行业。”
医疗保健和工程领域的受访者尤其可能看到美好的未来,比例分别为59%和55%。相比之下,只有38%的生态学和进化论领域从业者,以及40%的地质学和环境科学从业者持积极态度。这场疫情可能在不同领域造成了乐观和悲观情绪。美国的一位生物医学博士后表示:“我希望这次(疫情)能为生物医学科学带来更多的资金机遇,但我也认为它大大减缓了与SARS-CoV-2无关的任何研究的进度。”
与处于职业后期的研究人员(39%)相比,处于职业生涯早期或中期的研究人员(49%)普遍对职业前景感到更积极。可以想见的是,与全职的“合同工”(36%)相比,全职“永久”岗位人员的乐观情绪也更高(53%)。
固定期限合同给中国汕头大学环境化学家Edmond Sanganyado的未来蒙上了阴影。“在中国没有终身岗位”,来自津巴布韦的Sanganyado说。“你得每三年续签一次合同。外国人在这里很难建立长远目标。”
调查结果揭示的一片愁云惨雾,让佛蒙特大学伯灵顿分校的生物学家兼副教务长Jim Vigoreaux略感诧异。Vigoreaux在6月与人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为在研究型机构寻求教职的科学家提供了建议(J. O. Vigoreaux & M. J. Leibowitz BMC Proc. 15, 4; 2021)。
他承认教师职位供不应求,而且任何特定的申请成功几率都很低。但他指出,拥有科研技能的人在学术界内外有越来越多的选择。他说,诸如可持续性、社会正义和医疗保健等复杂问题将需要一支庞大而坚定的研究队伍。“我们面临许多巨大挑战,在那么多科学和技术领域都有极为有趣的领域。我不太明白人们为何那么消极。”
Vigoreaux鼓励处于求职阶段的研究人员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科学能干什么,在科学界和其他领域都可以作一番探索,但这并不代表申请工作时要无的放矢。“人们常有的心态是一通扫射看哪个击中了目标”,他说。“我建议不要这样做。付出努力时应当认真挑选。当看准一个机会时,要全力以赴放手一搏。”
受访者有理由感到怀疑。当被问及职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时,逾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争取经费是他们最大的忧虑,而且31%的人提到科研经费整体上是匮乏的(见“薪酬和职业前景”)。经费匮乏的问题尤其困扰西班牙(44%)、澳大利亚(53%)和巴西(64%)受访者。整体上,有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职业生涯因缺乏技能而受阻。当要求具体说说短板时,这些受访者特别提到了担心自己缺乏“硬”技能,例如对特定实验技术和计算机的熟练程度。
薪酬差距
调查发现,研究领域、工作类型和地域等因素导致了明显的薪酬差距。总体而言,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报告年薪酬超过8万美元,包括了年薪超过15万美元的7%。这一数字较2008年有所上升,当时23%的受访者报告年薪超过8万美元,只有5%的受访者年薪超过15万美元。而在人群的另一端,2021年调查发现有19%的受访者报告薪酬低于3万美元,这还包括了甚至低于15000美元的9%。
高薪在产业界确实比学术界更普遍。17%的产业界受访者表示每年的收入超过15万美元,这一薪酬水平在学术界只占比5%。美国的一位生物信息学家说,“找工作时候产业界提供的薪酬大概是我现在赚的2倍。如果学术界竞争力能和产业界相提并论就好了,但我喜欢我的工作和我现在住的地方,所以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不出所料,地理位置是薪酬差异的原因之一。超过一半的美国受访者表示其年收入高于8万美元。但这一数字在英国为19%,中国为6%,巴西仅为3%。Haas说,作为巴西的一名全职教授,她的收入甚至低于别处的大多数博士生。
总的来说,主要承担教学任务的受访者有27%报告其收入低于15000美元。值得注意的是,7%的全职教授也报告说年收入不到15000美元,这令学术有成的学者们深陷困局。阿根廷的一位全职生物医学教授感叹说,她所在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裁员后,自己每个月的收入仅为300~400美元。她写道:“多年来科学在阿根廷一直不受重视,情况还在越来越糟。”
与之前的《自然》调查一样,男性和女性研究人员报告的收入通常相似,尤其是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然而,担任高级职位的高收入者存在性别差距。在那些处于职业生涯后期的科学家中,有40%的男性研究人员和36%的女性研究人员报告收入超过11万美元。这一趋势呼应了2018年的调查结果,当时的数字是男性占33%,女性占23%。
薪酬似乎停滞不前。只有38%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年有过涨薪,低于2018年调查的51%。还有9%的受访者表示工资有所下降。当被问及减薪原因时,40%的人将其归咎于所在机构的裁员。这一评论在学术界(44%)更常见,几乎是产业界(23%)的2倍。
尽管与之前的调查相比,喜提加薪的受访者相对较少,但总体上仍有超半数(52%)的受访者对整体薪酬水平感到满意,这一数字比2018年的43%有所上升。其中,产业界受访者对薪酬的满意度较高,为62%,而在学术界,这一比例还不到一半。
低谷之渊
许多科学家完全有理由抱怨。俄罗斯的一位全职物理学家说自己年薪不到5000美元。“俄罗斯存在地区差异”,他写道,“科学家在莫斯科的薪水和欧洲差不多。”他表示在他所居住的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工资尤其低,他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薪并不总是意味着满足。美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项目经理表示,她对自己超过20万美元的薪水“无所谓满意或不满意”。她说所在公司存在一些超越薪酬的问题,包括“缺乏长期的制度目标、人员流动、决策流程不良和自上而下的沟通”。
有时,换个环境可以极大改善科学家的财务状况。物理学家Ana Rakonjac说,她在英国作为博士后的五年多时间一直苦于较低的工资,但当她开始在新加坡的原子物理学初创公司Atomionics担任高级研究科学家时,境况开始有所好转。“薪水要高得多,这很大程度缓解了个人压力。”她说。“博士后的薪水还可以,但想要存下钱就很难了。我从来没有过物质方面的安全感。一旦出了什么问题,我就得依靠父母。”
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员Joyce Main说,博士后的训练在短期内并不总能带来丰厚的回报,但长期来看可能是一项值得的投资,尤其是对于那些希望留在学术界的人来说。Main今年早些时候与他人合著了一篇论文,该论文使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库来跟踪美国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工程和医学(STEM)领域的博士后的职业回报(J. Wang & J. B. Main Stud. Grad. Postdoc. Educ. 12, 384–402; 2021)。
该研究发现,在社会科学或STEM领域完成博士后,增加了在博士毕业后7~9年里获得终身教职岗位的几率。她建议说:“在致力于你的研究计划时,博士后经历是有帮助的,因为这将提供给你一个专注于研究和发表论文的机会。”
Vigoreaux说,找工作时不专注的科学家往往难以拿到应得的薪水。“问题在于,他们会因为不安全感而即刻接受人家给的第一个报价。”他说,“他们没有做好技能准备去谈判一个好起薪。”他解释说,专注自身诉求的求职者会对想获得的收入有更明确的期望。
总体上,这次调查反映了多样化的科研经历(见“你如何看待你的薪水和职业前景?”),许多人的挣扎彷徨与另一些人的成功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位在政府机构工作、年收入超过11万美元的美国社会科学家总结了她的观点。“我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满足和乐观,但(我)非常清楚,与这个领域的大多数博士相比,我十分幸运。”
你如何看待你的薪水和职业前景?
《自然》对薪资和工作满意度调查的自由评论部分显示出科学家在薪酬和职业前景的担忧。这些评论为简洁起见经过了编辑或必要翻译。
我在学术界是一名相对成功的博士后,但我未来的职业前景并不好。根本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提供给博士后人群。产业界总是拒绝我的申请,因为我缺乏产业界经验,而且我做博士后的时间太长了。
——来自丹麦的生物医学博士后
我在英国的政府实验室工作。工资从2010年到2015年被冻结,与产业/学术界相差甚远。眼下又来一波工资冻结。如果不是要靠工作来补充养老金,我就退休了。
——来自英国生物医学政府实验室团队负责人
我很幸运找到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但我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如果我去拿个博士学位,我将背上更多的债,但赚的没什么区别。看起来不可能有所进展。我无法想象回去全职学习,同时能有办法支付学费。我想做自己的研究,但觉得这不可能。我得考虑赚钱生存。
——来自美国微生物学公司的科学家
提升文化、工作保障、稳定资金,人才会涌向科学。除非这个职业的基本人性得到改善,否则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不需要更多的问卷调查,而是需要在全球和集体层面采取行动。
——来自美国政府化学工作者科学家
印度的研究主要依赖于政府资助,除非私人资助和研究计划填补空白,否则情况不会改善。社会研究和以低成本开发提高福利的技术本应是印度研究的重点。
——来自印度生物医学的政府科学家
我所在学院的管理层每周给我支付一天的工资,却期望我全职工作。作为一名拥有超过15年经验的职业科学家,我对学术已经幻灭了。我的很多朋友都退出了学术圈,我也即将退出。我们绝大多数人只是被当作廉价劳动力。研究人员不仅需要钱来生活和发挥最佳能力,还需要得到对辛勤工作的认可。有些事情必须改变。
——来自澳大利亚生物医学博士后
考虑到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博士后的薪水简直是在侮辱人。没有博士后劳动力,任何大学都无法维持运转。住在大城市的博士后不应纳税,他们30多岁仍没钱一个人住,必须和别人合租。学术界正在变成一台铣床,毫不考虑生活工作平衡和公平待遇。
——来自美国生物医学领域博士后
作为法国的公务员,我已经有10多年没有涨薪了,这让科学职业越来越没有吸引力。我可以从生活水平中感觉到这一点,住房成本不断增加导致了工资变相贬值,让我们越来越难招到优秀的年轻同事。我完全理解他们会去其他地方追求更高的报酬和更多的资源。
——来自法国的农业和食品领域研究主任(译自法语)
原文以Stagnating salaries present hurdles to career satisfaction为标题发表在2021年11月16日《自然》的职业特写版块上,© nature,doi: 10.1038/d41586-021-03041-0
《自然》薪资和工作满意度调查每三年进行一次,上一次是在2018年。此次调查与伦敦的科研咨询公司Shift Learning合作,调查提供了英文、中文、西班牙文、法文和葡萄牙文版本,可获取调查的完整数据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ature Portfolio(ID:nature-portfolio),作者:Asher Mull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