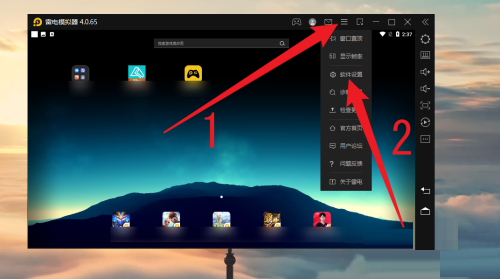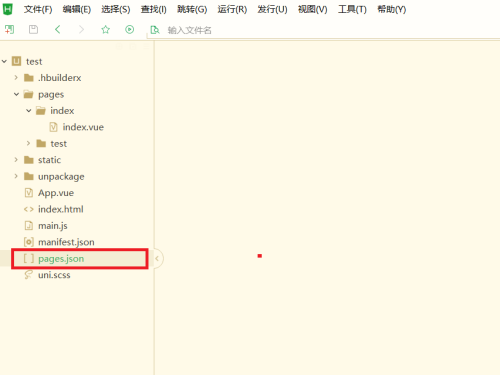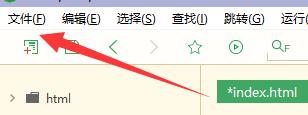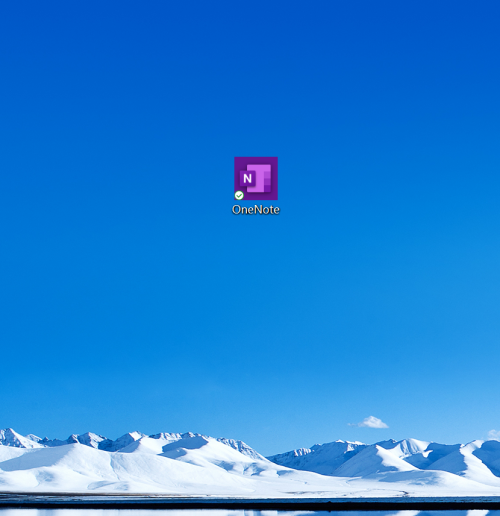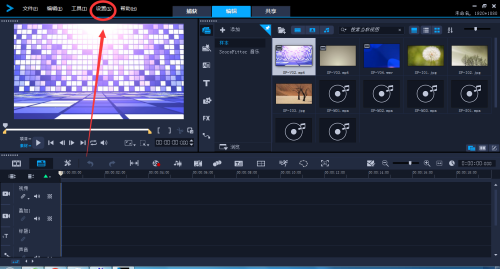到底什么是纯真呢?纯真其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空间,是我们强加于儿童的定义,是我们自己心理的投射,或者说是成年人自己的道德想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ID:yixiclub),作者:许晶(人类学者、儿童发展研究者),策划:通通,剪辑:傅昊,原文标题:《我们大概也会惊讶,小孩为何如此精明,三岁就知道要讨好领导了》,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大家好,我叫许晶,是一名人类学者,也是一个每天鸡飞狗跳在带娃的妈妈。我的研究重点是人类幼崽。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纪录片《幼儿园》,其中一段对话让我眼界大开。
截图来自纪录片《幼儿园》,导演张以庆。
对话戛然而止,但由此引发的思考却成为我研究的重要动因。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儿童的道德世界。
人类幼崽天生有道德吗?
你们可能会好奇,三岁孩子的道德世界是什么样的?很小的小孩有道德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下何为道德。从学术研究的角度,道德包括同理心、关爱他人、公平观念、互惠、个体自由与尊严、遵从等级与支配关系等等。
一派观点认为,孩童与生俱来有道德天性。比如我们熟悉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可是另一种观点,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人的心灵初始状态如同白纸一张。甚至在发展心理学之父皮亚杰看来,六岁以后儿童才有道德感。
直到21世纪,科学家才能用实证的方法系统地研究婴幼儿的道德认知。我们可能会好奇,科学家怎么知道婴儿的所思所想呢?大一点的孩子或者成年人他们会说话会写字,我们可以做访谈,可以做问卷调查,可以分析他们的文字记录。
那科学家在实验室如何研究婴儿呢?实际上,婴儿的眼睛会说话,科学家通过监测婴儿的注视时长和他们的行为选择,来推测他们的思维世界。
接下来我介绍几个实验。就是这些实验让大家重新认识到,原来婴儿就有了道德意识的萌芽,比如说善恶。
有一个著名的实验,研究者给6个月大的婴儿看社会互动的情景。这个情景是一个红色的小人在爬坡,很努力地爬,但是爬不上去。
实验人员再给婴儿观看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结果是一个蓝色的方块小人跑过来,从坡底下把那个红色的小人往上推,帮助他完成目标。
另一种结果是一个三角形的黄色小人跑过来,站在坡上把红色小人往下推,阻碍他实现目标。
看完结果之后,实验人员把三角形小人和方块小人都放到婴儿面前,让他们选择更喜欢哪个。实验人员发现,大多数婴儿都会选择那个帮助人的蓝色的方块。
科学家由此推断,小孩在婴儿时期就有了某种分辨善恶的雏形。
还有一个关于等级的实验。科学家给10到13个月的婴儿观看了一个情景。在这个情景里有两个小人,一个小人个头大,一个小人个头小,他们要实现各自的目标,但是他们挡了各自的道路,所以两个人物的目标发生了冲突。
随后,科学家给婴儿不断看这样的场景,直到婴儿熟悉了为止,接下来再给婴儿观看两种不同的结果。
第一个视频里,婴儿看到的结果是,个头小的给个头大的让道。
第二个视频里,婴儿看到的是相反的,个头大的给个头小的让道。
实验人员通过婴儿的注视时长来推测婴儿的动机,注视时间长说明婴儿对那个结果表示惊讶,感到新奇,不符合他们本来的预期。
实验人员发现,婴儿在观看后一种情况时,注视时长明显更长。也就是说,个头大的给个头小的让步,他们感到惊讶,违反预期。
科学家由此推断,婴儿从这个时候起,就有了某种对于社会支配和等级观念的雏形。这里需要提醒一下,这个结果可能跟我们文化中强调的谦让观念(比如孔融让梨)不一样,动物界的天性就是强者支配弱者。
第三个实验关于公平观念,也是利用了婴儿的注视时长。实验人员给15个月大的婴儿看了一个社会分配的场景,两个人分饼干,一种结果是平均分配,另外一种是不平均分配。
实验人员发现,婴儿对于不平均分配的结果(右图)感到惊讶。
大家可能会想,也许婴儿只是因为两边数字不对称而感到惊讶呢?所以,实验人员又做了一组对照实验,同样的分配结果,只是把桌子两边的人,换成了两个枕头。这个时候,婴儿注视时长的差别就消失了。这说明,婴儿的选择的确是针对社会情境分配关系的。人类在婴儿时期就有了对于分配公平的理解雏形。
综合上面的实验,我们可以看到,成年人习以为常的一些道德认识,其实在婴幼儿时期就初具雏形,或者说,婴儿真的与生俱来有某种道德天性。
科学家还把类似的实验推广到了灵长类的研究,发现很多这样的能力,包括公平观念、等级、互惠互利等等,灵长类动物也具有。
下面我介绍一个关于灵长类对分配公平理解的实验。科学家对南美洲卷尾猴做了实验。通常情况下,猴子们拿一个小石头就能够获得实验员的奖赏。一般奖赏就是黄瓜片,它们就很满足了。但是在这个实验里面,科学家把两个猴子放在一起,给它们分配了不同的奖赏。
当一只猴子看到自己的奖赏是黄瓜片,而同伴的奖赏是葡萄——明显更好的食物时,它就把黄瓜片砸向实验员,以示抗议。
科学家推断,灵长类动物在社会对比的情境中意识到分配不公,这说明它们对于公平观念是有某种理解的。
所以不管是人类婴儿还是灵长类,都有一些关乎群体生活秩序的雏形的认识,这些能力也受到生物演化的影响。
我们用“道德能力”来描述这种“天性”,它是一种隐而未发的心理预备。我们可以用语言来做类比。儿童生下来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天生就有学习语言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是儿童习得母语的基础。
很多年前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我读到卢梭的《爱弥儿》开篇:出自造物主手里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的手里就变坏了。当时我非常惊讶,热血沸腾,我特别想要搞清楚,到底是这样吗?是本来一些天性都是好的,到了环境中就变坏吗?
后来,我们看到,其实“天性”和“后天经验的养成”不是对立的,也不是互斥的,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世界各地的儿童道德养成
儿童的道德是一个丰富的世界,可是世界各地儿童的道德养成是一样的吗?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人类学家的工作。人类学家带着跨文化的视野来研究童年。
比如,加拿大西北部因纽特部落的人很少批评责骂小孩,而是通过一种很特殊的教育方式,叫morality play,也就是一种戏剧的方式,让小孩在嬉戏游乐中做角色扮演。
在游戏中,成年人可能会问一个三岁的小女孩,你会杀掉你的弟弟吗?成年人就是在这种玩乐的方式里面引导小孩体验各样的情感困境,去做出道德选择,也激发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与他人共情。
在西非的Bayaka部落,信奉平等主义,他们最神圣的文化价值就是个体的自主权,所以当地人特别尊重小孩,哪怕是婴儿的自主意识。比如说小孩在火旁玩耍,他们拿着砍刀玩,大人都不会去制止。
道德心理学家Jonanthan Haidt用过一个比喻,他说,多元道德就像我们人的味蕾,我们天生就具有识别酸甜苦辣各种不同味道的能力,但是不同环境的培养使得我们慢慢趋向某一种味觉。
那么,在中国,儿童的道德发展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带着这样的思考,我开始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后来这篇论文编成了一本英文书,在2017年出版,名字叫The Good Child,中文版也在去年与大家相见。
我想特别提一下,英文版这个封面的小孩是我的儿子,小名豌豆,这张照片是他两岁的时候。他当时就是这个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也是我的研究对象之一。
从2011年到2021年,我在华东某一线城市的一所中产阶级私立幼儿园里进行了一年的田野调查。我从小班、中班到大班,在每个教室里面蹲着,观察小孩,成为他们的朋友。他们亲切地叫我“许老师”。
除了观察小朋友,我还对家长和老师做了访谈,也给家长发放了有关育儿理念和实践的调查问卷。除此之外,我还加入了几个心理实验,找了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参与这些实验。
下面我就讲几个故事,来给大家展现一下幼儿园里面的人类幼崽的道德世界。
“拉关系”
第一个故事有关分享。我们一想到要教导小孩子关爱别人,通常会鼓励小孩子去分享。
在我做调查的时候,幼儿园大多数小孩是独生子女,家长和老师都很担心独生子女太自私、太自我,于是他们特别强调分享的教育,他们会强调要小孩分享零食,分享玩具,而且他们所教导的是一种无差别的分享,就是不管怎么样,小朋友都要分享。
成年人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教导小孩,让他们带零食带玩具来与小朋友分享。每个小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家长会送一个蛋糕到学校,班主任老师会把蛋糕平均分发给班里的小朋友。
有一天,三岁的成成过生日,老师分好蛋糕发给班级同学的时候,成成突然看到他们园长从教室窗户旁边走过。其实园长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班级里发生了什么,但是成成突然跟他的老师说,老师,你怎么不给园长分一块大的蛋糕呢?你知道吗,你要讨好领导的,你要跟你的领导套近乎。
当时老师都懵了,她就跟我说,三岁的小孩就知道要讨好领导了。老师就给这个小孩起了个名字叫“魔童”。我们大概也会有这样惊讶的反应,小孩为什么会如此精明,三岁就知道要讨好领导了?
但是与其做这么直接的价值判断,作为人类学者,我更感兴趣的是小孩子自己是怎么想的。
小孩子为什么要分享呢?人类学演化认知理论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分享是出于无私利他的动机;另一种认为分享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行为,出于跟别人建立合作关系的动机。
于是,我就设计了心理实验来考察小孩行为背后真实的思想意图。我给小朋友做了一个分糖果的实验。在研究的时候,所有实验我都会跟小朋友说是“跟我来玩一个游戏”,他们也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愿意参与。
实验
有19位小朋友参加了这个游戏,他们在两到三岁之间,小班的年纪。首先,我给了他们一个简单的画图的任务,画好了以后我给了他们两块糖果以示奖励,然后我就问这个小朋友,你可不可以把一块糖果分享给另一个小朋友?
如果这个小朋友说愿意,接下来我就会跟他讲一个故事,再问他要分享给哪个小朋友。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有两个小朋友来到我们幼儿园玩,有一个小朋友只是来参观一下,明天就不在这了。另外一个小朋友要转到你的班里,成为幼儿园的新生,明天就正式和你们一起上学。
讲完这个故事以后,我会问参加实验的小朋友,你要分享给哪一位呢?这个小朋友如果做出了选择,我会试着去问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最后,我会拿两个信封包住糖果,问参与实验的小朋友,要不要在信封上写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结果。首先,19个小朋友都跟我说他们愿意分享,非常爽快。
其中,14个小朋友选择分享给留下来的小孩,5个选择给给离开的小孩。他们给的理由也很有意思,有的说因为留下来的小孩可以跟我做朋友,将来也可以把东西分享给我。
19个小朋友都选择了非匿名赠与,想在信封上写着自己的名字,想让对方知道是谁分享的糖果。这些结果说明,小孩子并不是平等无差别地分享,他们的分享里包含互利互惠的动机。
我在平时的观察中也发现,小孩子对于分享特别在意,他们清楚记得分享交换物品的历史,记得谁给了他们什么东西,谁没有还礼。他们这种想法也不全是一种理性计算或者策略考量,也饱含着情感的色彩,可以说物品的分享和交换是小孩子的世界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管是分糖果的实验,还是成成在生日会上的表现,都让我们看到:这些小孩其实深深懂得老师家长的教导,但是有别于家长老师的教导,他们有自己的应对方式和行为逻辑,他们都有互惠互利的考量。
大人看到小孩子的行为与自己预期不一样,一旦他们的分享不是从纯粹关爱别人的视角出发,我们好像就会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不纯真,甚至是有心机的“魔童”。
那到底什么是纯真呢?纯真其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空间,是我们强加于儿童的定义,是我们自己心理的投射,或者说是成年人自己的道德想象。
实际上,互惠互利是非常天然的一种行为,我们看到动物界,我们的近亲灵长类也很有心机。
灵长类的理毛行为就体现出了互惠互利的特点。2008年有一个研究统计,包括22个物种在内的48个社群中,雌性灵长类偏向于对那些给自己理毛最多的同类予以理毛回馈,这样不光是对自己的亲戚,也是对朋友的互惠。为的是建立合作联盟的关系。
公平与“表现好”
从刚才的实验我们能看到,平等分享似乎不是幼儿园小孩眼里的公平观念,那他们有什么样的公平概念呢?
绩效公平和平等分配都是分配公平的重要原则。2010年初,科学家才系统地发现,人类在幼儿期就萌生了对于绩效公平的理解。
那孩子们的公平概念是怎样受到教育文化的影响呢?我做了另一个实验,我把这个实验叫做分饼干的游戏。这个实验是中国和日本的一个比较实验,也是欧美以外第一次做这样的研究。
实验
跟分糖果的游戏类似,我也是请小朋友一个个地来跟我做这个实验。我给参加实验的小朋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小女孩一起做饼干,有个小女孩一直坚持到最后,另外一个小女孩做着做着有点无聊,就出去玩,玩了以后再回来接着做。最后,她们两个人一共做了三个小饼干。
讲完这个故事以后,我拿了一个纸盘子装着三个剪纸做成的小饼干给参与实验的小朋友,然后问他们要怎么样去分配。
分配有两个阶段。首先是让他们自由分,把这三个饼干分给两个小女孩。分完了以后,如果还有一个剩下的,就进入最后分配阶段。最后分配的时候,他们务必要把三个饼干都分给两个小女孩。
分配的结果有三种。一种是平等,就是在自由分配阶段每人分一个。一种是绩效,两个饼干分给那个一直坚持做饼干的小女孩,一个饼干给那个中途出去的小孩。第三种是反绩效,也就是两个饼干给了中途溜号的小女孩,一个饼干分给坚持做下去的。
我们来看一下实验结果。在自由分配的阶段,大多数中国小朋友出现了两种分配情况,一种是绩效分配,一种是平等分配,很少是反绩效分配。在最终分配阶段,大多数小孩都选择了绩效分配,拿了两个饼干给那个一直坚持做饼干的小孩。
我们来看一下中日对比。
横轴代表分配模式,纵轴代表选择这种分配模式的小孩数量。
很有意思的是,在自由分配阶段,中国小朋友选择“平等分配”和“绩效分配”的人数势均力敌。
但绝大多数日本小朋友都在自由分配阶段选择了平等分配,他们选择了一人给一个,然后剩下一个饼干不分。
只是在最终分配阶段,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小朋友,他们大多数小孩都选择绩效分配,两个饼干分给那个一直坚持在工作的小女孩。
自由分配和最终分配,其实考察的是两个不同的心理状况。自由分配考察的是儿童的偏好,如果让他们来选择,他们会怎么选。而最终分配考察的是他们有没有能力做绩效的分配。
所以我们看到,实验中的中国小朋友在偏好上就已经倾向于多劳多得的绩效分配了。
这是为什么呢?有一天做实验以后,幼儿园一个小孩的家长就问我,你们这个实验做了什么?我就把实验的流程讲给他听,然后他说了一句,学校里面教的净是这个,做得多的,得得多。
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于是我就来观察小朋友是怎么样知道绩效公平的。我把这种文化或者教育的影响叫做“表现好”。
豌豆是幼儿园最小的小朋友,他刚入园时并不知道贴纸是什么。过几天,老师为了安抚哭闹的小孩,就给他们奖励贴纸,额头上贴一个贴纸就是莫大的荣光。从此以后,像豌豆这样的小朋友从两岁开始就学会说“表现好”,他们会说“谁谁谁表现好”,“谁谁谁表现不好”。他们理解了老师的这种奖赏和惩罚,也理解了里面蕴含的等级关系。
对他们来说,老师奖的贴纸具有迷之吸引力,甚至在豌豆小时候,他会把水果上面的标签撕下来贴在自己的额头上。然后我问他,这是老师奖给你的吗?他会点点头,说是老师奖的。
我们看到,这种“表现好”的教育,给小孩的认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实验里面他们会自发地运用这种话语,比如有的小朋友故事还没听完,就会问我,哪个小女孩表现好?或者还没有听明白就说,“这两个小女孩表现好,老师给他们奖励”。
可见,他们把对于“表现好”的根深蒂固的认识融入到心理实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分配公平的理解,其实受到了等级权威关系的影响,他们在这样的等级权威关系里认识自我、评价他人。
我就在想,幼儿园的小朋友怎么样才是表现好呢?托班的小孩可能不哭不闹就是表现好,好好坐着、能够排着小火车,就是表现好。可是到了中班、大班,慢慢地,学习好变成了至上的标准。我记得在实验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会跟我问,哪个人学习好?这都是实验里没有的情节,但是小孩就会脑补这样的画面然后来问我。
说回豌豆,他还记得什么是表现好吗?
2011年跟我回国的时候他不到两岁,到现在一晃十年了。现在,他在西雅图的小学不太注重学习成绩,也不太讲这样的话语。疫情期间跟在国内的外婆视频的时候,外婆就会问,豌豆,你今天表现好不好?豌豆,今天老师有没有表扬你?豌豆,你要好好学习。豌豆会翻着白眼说,妈妈,外婆只知道讲学习。
豌豆的小学没有什么家庭作业,课堂作业如果完成得好,老师会给出“Good job”的评价,即便完成得不好,哪怕是一张白卷,老母亲心哇凉哇凉的,豌豆会跟我说,老师都说了“It is fine”。
在他们的观念中,虽然没有“表现好”这样的概念,但是豌豆会说,“我们的老师说了,科学家研究发现,做作业对小孩子没有好处,所以我们不要做作业。”
这样的语言也表示,他其实对老师这个权威的概念也是深信不疑的。他们其实也有“表现”,也讲绩效公平,只是强调的方面不一样罢了。
其实绩效公平也好,表现也罢,都是我们自然天性里面的逻辑,本无可非议,可是问题就在于,什么样是表现好?什么样的绩效是对的?我们是要鼓励小孩从婴儿期就开始竞争内卷呢,还是尊重儿童的主体性鼓励参差多态呢?
同理心的困境
最后一个故事关于同理心。
同理心也叫共情,同理心的本质就是我们能够与他人产生联结,能够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状态。科学家最近发现,其实人类从婴儿时期就有了基本的共情的反应,能在他人受到苦痛的时候有安慰、怜悯的情感。
这种情感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情绪传染,并不是一个小孩看着另一个小孩哭自己就难受,这种共情是出于对他人的一种关爱。小孩会帮助别人、安慰别人,这种帮助和安慰是想要看到对方的情绪得到缓解,是内在驱动的。
这好像为我们描绘了一出特别美好的画面,但实际上,同理心也是有边界和局限的。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天生有与他人进行情感联结、感受他人苦痛状态的能力,但是随着小孩慢慢成长,神经科学家发现,他们会从这种初始的自发的情感反应,转变成一种认知理性的评估。
我做田野的时候,大众舆论充斥着对于社会道德状况的担忧,比如助人反被讹,比如批评人心冷漠、缺乏同理心,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小悦悦事件”。这些新闻议题呈现出一种矛盾,在紧急状况下,发乎天然的共情与关爱如何溃败于对风险和自保的理性计算。
老师和家长也处在一个矛盾中:他们都觉得同理心很重要,希望孩子们纯真善良,也努力培养这样的品格,但同时又害怕孩子会因为纯真善良而吃亏,受到算计,会受挫。
我曾跟幼儿园一个小男孩的爸爸说:“你儿子很善良。”他父亲却叹了口气,沮丧地说:“但是一个善良的人在当今社会无法生存。” 这个场景令我印象深刻。
育儿者会向孩子们传达自相矛盾的期望,这也会影响孩子们同理心的发展。我不禁想,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这种矛盾的信息和体验,会如何影响小孩和我们所有人的同理心的发展,在什么情境下小孩需要抑制那种原初的共情的感受,不去关爱他人。
甚至科学家也出了这样一本书,叫Against Empathy,认为同理心是有边界的,人类天性的善也是有局限的。
什么是“好孩子”?
回到最开始的《幼儿园》里的小男孩,是不是分一点给领导就是有心机呢?是不是跟领导套近乎就是“魔童”呢?拉关系就不是好孩子吗?老师和家长们也很矛盾。
2012年六一儿童节,幼儿园每个班都要出集体舞蹈,有一个班上场的时候,领舞的小男孩突然紧张大哭,周围的观众一片哄笑,场上其他小孩也是各自忙着找自己的位置,无暇顾及。只有一个小孩回头看这个正在哭泣的同学,抱以同情的目光。
这件事情在家长和老师之间引起了很多讨论,有的家长就会自责,为什么我没有教育自己的孩子对哭泣中的同学抱以同情?但也有老师很心疼,觉得这个小孩太纯真了,担心他将来会受欺负的。
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焦虑。在这样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里,到底是培养一个有德行的孩子呢,还是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处处讲合作,与人为善,看上去很美。但我们又会担心,将来面对那种强大的竞争者,他们会不会一败涂地、沦为炮灰呢?很多家长都陷入了这样的囚徒困境。
作为一个母亲,我也时常迷茫和焦虑,我也时常评价自己的孩子,也会担心在复杂的环境下他会怎么生存。
可是我们知道,道德的天性真的是丰富多样,每个小孩都带着自己独特的基因和灵魂来到这个世界里,小孩生长的环境是千变万化的,甚至是我们育儿的观念、我们自己的想象,也被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力量所塑造着。
我想,与其焦虑如何培养好孩子,不如跳出这种成年人的框架、成年人的想象,暂时抛开我们与孩子,家长与儿童之间的这种权力关系。用一个观察者的视角,观察者的谦卑和好奇心,来认识作为道德主体的儿童。与其焦虑如何培养好孩子,不如去思考我们如何创造一个好孩子能够自由生长的社会环境。
最后,我想改引纪伯伦的诗句结尾——
“我们的孩子都不是我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是借我们而来,却不是从我们而来。他们虽和我们同在,却不属于我们。”
谢谢大家。
参考文献
[1] 许晶,《培养好孩子:道德与儿童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2] Xu, Jing. The good child: Moral development in a Chinese preschoo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3] Chevallier, Coralie, et al. "Preschoolers’ understanding of merit in two Asian societies." Plos one 10.5 (2015): e0114717.
[4] Hamlin, J. Kiley, Karen Wynn, and Paul Bloom. "Social evaluation by preverbal infants." Nature 450.7169 (2007): 557-559.
[5] Schino, Gabriele, and Filippo Aureli. "Grooming reciprocation among female primates: a meta-analysis." Biology Letters 4.1 (2008): 9-11.
[6] Schmidt, Marco FH, and Jessica A. Sommerville. "Fairness expectations and altruistic sharing in 15-month-old human infants." PloS one 6.10 (2011): e23223.
[7] Thomsen, Lotte, et al. "Big and mighty: Preverbal infants mentally represent social dominance." science 331.6016 (2011): 477-480.
[8] Xu, Jing. "Tattl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rm Sensitivity, Moral Anxiety, and “The Genuine Child”." Ethos48.1 (2020): 29-49.
[9] TED Talk: "Frans de Waal: Moral behavior in animals."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ID:yixiclub),作者:许晶(人类学者、儿童发展研究者),策划:通通,剪辑:傅昊,设计:四九